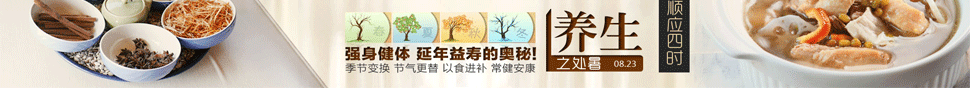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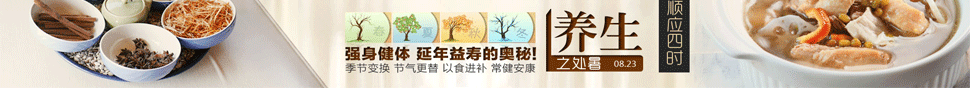
行走的课堂,与到此一游的踩景点究竟有啥不一样?
是导游的不一样?换了是一个精通信仰文化历史的人?
把景点赋予多一层宗教的联系和意义?
很多时候,姜老师的课堂除了有故事外,他还会让我们在现场去感受。例如在利玛窦墓园,他让我们各人安静漫步,跟这群传教士聊聊天,把想说的跟他们说。
不是听完故事,拍完照就离开。这段独特的个人时刻,把我们自身与现场、历史奇妙地联系起来。同时,也让我们应着现场环境分享、表达感受,这便是体验学习的核心价值——解说(debriefings)——透过参与者的个人领受来丰富彼此的学习,对课题有多角度,以及不同层次的追问和挖深。
六月份两次行走的课堂:十字寺与利玛窦墓,虽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现场,但两处遗址背后都记载和代表着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两大时期。
(利玛窦墓/左,十字寺石碑/右)
首先是唐代的景教,也是基督教最早进入中国的记载,十字寺成为了外来信徒敬拜、静修之地。
回看景教的在华历史,我们发现,这次的传入是相对较“单向度”的进入。景教在华期间并没有形成一个文化核心,与中国文化进行彼此深入的了解和交流,尤其没有促进深入的对话。
所以,景教的失败,除了当时社会政治和民族政治等因素外,其最基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没有实现景教与中国文人文化的深入对话。他们把信仰带到中国时,太过急功近利,以致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过于中国本土化,甚至乎过于佛教化。一般人很难分辨景教和佛教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导致在后来的灭佛运动中,把景教也泱及了。
反观明朝时的耶稣会士,他们在华期间,把精力放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社节习俗上,再加上教士们都是学识渊博的年青学者,他们更成为西学东渐的先行者。
以利玛窦为例,他当时给自己的称谓是”predicatorelitterato”,中文直译为“有文化的传道人”。除了宗教外,他具有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在华期间,还致力与官绅阶层进行密切交往和友好对话,他所到之处,都得到中国官员的信任。据说他进京前,在南昌任教三年间,他从对话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这对他日后在北京的传教工作,帮助不浅。
当他获万历皇帝重用留京期间,他进一步把西方知识与当时的朝廷官员分享,透过对文化的探讨和对话改变了当时的一众知识分子。
在宣武门的天主堂内,他设立西方图书馆和举办科学仪器展览,吸引大批官员和儒士参观,当中徐光启、李之藻因着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趣,与利玛窦一起研究天文、地理和历法,因而入教成为信徒。
原宣武门天主堂
现宣武门天主堂
“交流”和“对话”成为了两个时代基督教在华的明显分野。
利玛窦与当时的传教士身体力行,透过在华的生活,促进了彼此的认识,进而在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和对话,让“交流”和“对话”的种子在中国生根成长,培育了一代本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徐光启便是其中最为显赫的一员——在学术界里,他是中国现代科学第一人(数学家、天文学家、农业学家和政治家)。从他开始,带领中国人开始真正地了解世界。身为基督徒,他更是第一个本土神学家,他对基督教信仰和儒道释的不同,进行了持续而深入地梳理。
(利玛窦/左,徐光启/右)其实,只要我们愿意细心阅读和聆听,历史也是无时无刻在跟我们交流和对话。至少,这次十字寺和利玛窦墓的行走课堂,让我发现到“交流”和“对话”是改变的动力。
推荐阅读:党校里的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
春游十字寺——基督教中国教会史现存第一圣殿遗址(1)
燕山深深十字寺——春游十字寺(2)
守林人眼中的十字寺四季胜景——春游十字寺(3)
艺术家眼中十字寺的晨昏昼夜——春游十字寺(4)
盛宴诗人的嚎叫与十字古寺的凝望远行记忆之四
深山古树的叹息和守殿弟兄的祈祷——远行记忆之五
马槽原野
关于姜原来作品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