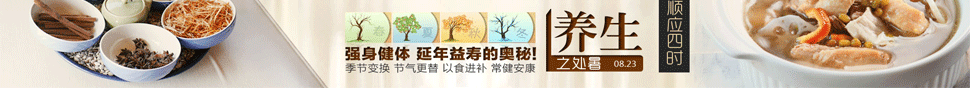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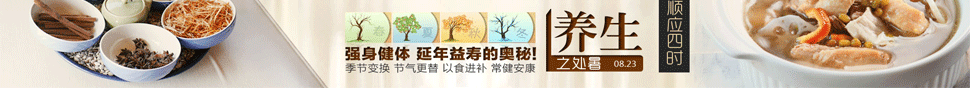
法国画家保罗·高更是后印象派“三大巨匠”之一,他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半路出家开始画画,一心寻找“人的本真”,到塔希提岛旅行后被那里的风土人情吸引,从此找到了精神家园,完成了创作风格的重要转变,留下许多关于塔希提的绘画与文学作品,而塔希提也因高更增加了更浓郁的色彩。
保罗·高更(—)同塞尚、梵高并称为法国后印象主义的“三大巨匠”。塔希提岛(Tahiti,又称大溪地)位于南太平洋中部,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有着典型的热带风光,四季温度适宜,阳光明媚,海水如水晶般晶莹剔透。早在18世纪被欧洲人首次发现后,塔希提便因伊甸园般的环境和岛上居民原始淳朴的生活方式声名远播,不少艺术家和作家都曾到此度假或寻找创作灵感,如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等,其中最为之着迷的当属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PaulGauguin),他不仅在塔希提生活多年,还对那里产生深厚感情,找到了真正的创作源泉。到塔希提去寻找人的本真年6月7日,高更在巴黎诞生。由于革命的爆发,他们一家搬到秘鲁生活。高更的父亲英年早逝,母亲在高更的祖父去世后带他返回法国,寄居在高更的叔叔家。童年时的海上经历和南美风情一直深深印在高更的脑海里,使他从小就有着强烈的旅行欲望。他曾在看到一张画着旅行者的雕版画后“离家出走”,幸被人“捡到”送回家。17岁时,高更决定退学,到商船上工作。他游历了巴西、巴拿马、大洋洲、东地中海和北极圈,享受着自由。20岁时,他告别大海去服兵役,3年后退役,开始到银行工作。高更旧照(年)高更生性乐观,总是对生活充满信心,做事主动性强,给同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很少像大多巴黎年轻人那样参与政治和社交,而是常在工作之余独自看书,还喜欢到舞厅跳舞。如果非要探究高更是什么时候和绘画产生了联系,那可能是在他和同事埃米尔成为朋友后。埃米尔爱画素描和油画,还收藏了一些名家画作。不久,高更认识了梅特-索菲·加德(Mette-SophieGad),被她的独立性格和聪明才智深深吸引。年11月,二人举行了婚礼,次年他们第一个孩子诞生。年,高更和妻子梅特-索菲·加德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在孩子出生前几个月,高更突然开始作画。一开始,他并没有明确的艺术目标,主要是认真临摹。他常到展览会上观察画作,参加艺术沙龙,被米勒画作中呈现的原始力量、生命活力、茂盛的自然所打动。高更体会到了绘画的难度,但他乐于享受这种挑战,还将一幅画作送到沙龙展出,竟被接受了。他渐渐发现了画画的价值,便常在下班后拜访画商,通过他们结识了许多艺术家,眼界越来越开阔。从此,高更过上了“双重生活”,一边在证券交易所的生意上取得很大成功,一边在印象派画家卡米耶·毕沙罗和爱德华·马奈的指导与鼓励下在绘画上取得进步。35岁时他从银行辞职,全心投入到绘画事业中。高更在巴黎的绘画之路并不顺利,画商们不肯为他提供机会,他亦难对风靡一时的印象派产生兴趣。他想把主要精力放在人体肖像的创作上,真实地刻画人体的原始美,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是很确定在巴黎无法实现自己的想法。于是,他挈妇将雏去了鲁昂,不久又迁往梅特的家乡丹麦。身在异域,高更没有模特,创作受阻,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出现问题,梅特不得不出去工作。梅特的家人对高更很冷漠,在漫长的冬季,高更常常独坐在一间小屋里画自己的肖像。他“全心全意地恨着丹麦”,认识到要想继续艺术生涯,必须离开这里。年6月,高更带着儿子重返巴黎,可他带去的画无人问津。高更认为印象派过于拘泥,而这与巴黎艺术圈的主流观点相左。他与毕沙罗等人筹备了一场画展,虽然没有轰动巴黎画坛,但他画作中单调而独特的色调引起一些画评家的注意。可是,高更依然囊空如洗,不得不出卖一些藏品。高更认为,社会的罪恶源于文明。在巴黎世博会美展上,高更发现了爪哇美术,又一次勾起了他对原始艺术的向往。他决定离开令人窒息的欧洲艺术氛围,到“蛮荒之地”寻找人的本真。年4月底,高更满怀期许登上了“马赛号”,前往心目中的自由之土。“诺阿诺阿”,一片“芳香的土地”高更从小就有热带情结,他的童年是在秘鲁利马度过的。他喜欢称自己是“野蛮人”,也的确拥有黝黑的皮肤和轮廓鲜明的五官,内心始终保有对原始荒蛮之地的向往。高更对位于海洋中间的塔希提岛极为钟情,在他的想象中,塔希提岛没有冬天,在那里生活不需要钱,不管欧洲发生怎样的变化,塔希提人“只会用自己的双手在肥沃的土地上寻找食物”。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法属波利尼西亚的首府帕皮提已经“感染”了高更本要逃离的欧式审美观念,充斥着欧洲工厂,当地种族的特色几近抹去。不过,当夜晚来临的时候,高更还是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寂静,这里甚至听不到一声鸟鸣,到处是干燥的落叶,让他得以尽情地释放心灵。逗留数周后,高更发现自己无法融入当地的“野蛮人”圈子,也无法激发艺术灵感,他决定走出帕皮提,远离欧洲人中心,来到塔希提南部的马泰阿镇。
高更租了小木屋,它位于山地和海洋的交界处,四周环绕着椰子树和面包树,透过栅栏能看到闪闪发光的海滩和轻拍海岸的浪花,小屋后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生活在这里的毛利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宁静祥和气质,有着强壮有力的四肢和黝黑发亮的皮肤。这正是高更追寻已久的平和,他沉睡的艺术梦想终于再次被点燃,不满足于仅仅捕捉毛利人单纯的美丽,还花了很长时间去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探索、理解他们对神秘事物的表达。
当然,高更也感到了孤独和空虚。他遇到了女孩泰瑚拉,尽管早已娶妻生子,但仍娶了她(未举行仪式)。更重要的是,泰瑚拉成了高更灵感的源泉,高更为她画了《沙滩上的塔希提女人》(FemmesdeTahiti)、《甜蜜的白日梦》(Joiedesereposer)等作品。泰瑚拉还是高更与当地人之间的桥梁,使他真正入乡随俗,“像他们一样吃,像他们一样穿”,每天赤脚走路,身体也差不多是裸露的,不再害怕阳光,晚上还去参加邻居的聚会,逐渐能听懂当地的语言,越来越对这个智慧的民族充满敬意,而邻居们也几乎把他看作家里人。尽管经济越来越拮据,但高更感到生活前所未有地踏实,“文明慢慢从身上消退,思想也变得单纯了”。近1年里,高更画了40多幅画,感觉自己已捕捉到土著人的神韵。他在给妻子梅特的信中写道:“我对新近完成的作品非常满意??我向你保证,我目前所做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我是唯一。法国没有人尝试过。”
年,高更在塔希提拥吻情妇泰瑚拉。DanielBlau摄《沙滩上的塔希提女人》。画中两位坐在沙滩上的土著女人,一个闭目养神,一个略带疑惑地看向别处,黄沙、绿海、红衣,通过大面积的平涂色块和强烈的色彩对比,显现出令人向往的野性之美。《甜蜜的白日梦》。高更用明细的线条、强烈的体积感和生硬的色彩对比描绘了塔希提岛的原始风光、淳朴的当地人及其无忧无虑的幸福感。
但是,高更在内心深处依然希望在欧洲得到肯定。年,由于家里有急事,高更返回法国。他说:“我在岛上过了两年,却似年轻了20岁,也更野蛮,然而更有教养。”
回到巴黎后,高更举办了一次画展,展出自己在塔希提的作品。参观者络绎不绝,他们能感受到高更作品中表达的新鲜思想和力量,但大多数人难以透彻理解,只是认为其题材太新颖、颜色太鲜明、技法太爽直。虽然也赢得了一些崇拜者,但高更并没有成功卖出几幅画,他的生活再度陷入困顿,“再也不想留在文明世界”。这一期间,他整理了在塔希提写的散记,汇成了《诺阿诺阿》(NoaNoa,意为“香啊香”)一书,对塔希提的原始生活进行了理想化和浪漫化的描述。
年2月底,高更再次前往塔希提。他在岛上重抄《诺阿诺阿》手稿,并配上了一系列水彩画、木板雕刻和照片。高更曾告诉妻子,这本书对理解他的绘画很有帮助。
高更在塔希提岛写的散记《诺阿诺阿》插画
这段时期,高更在创作中更多地融入了哲学性思考。年,他在得知挚爱的小女儿因肺炎死亡后,受到沉痛打击,昼夜不分地创作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Doùvenons-nous?Quesommes-nous?Oùallons-nous?),画名引用了帕斯卡的一句名言。同时,与第一次在塔希提相比,高更更深入地参与到当地的生活中。他给《胡蜂报》当记者,言辞激烈地批评岛上的官员,甚至自己出版了一份图文并茂的讽刺小报,在当地掀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
年,高更离开了塔希提,迁往更为原始的马克萨斯群岛。他在郊外买了一块地,自建“乐屋”,更加勤奋地写作、画画和制作陶器面具。年,由于号召土著反抗殖民政府,当局控告高更犯诽谤罪与煽动无政府主义罪,法院判处他监禁和罚款。高更不服,然而,还没来得及上诉,他就在5月8日突发心脏病去世。临终前,只有几个土著老人陪在他身旁。第二天,高更被草草地葬在天主教的公墓,遗物有的被寄回巴黎,有的被拍卖。
高更博物馆旁的纪念品商店售卖的高更画作衍生品
回想高更的一生,他有10年时间是在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度过的,而在塔希提那片“芳香土地”上的两段时光应该给了他最多的快乐,不仅因为他在那里创作了许多巅峰之作,更因为那里像他在《诺阿诺阿》书中所写的那样,“没有令人窒息的樊笼??是空间,是自由”。
追求原始味道的艺术在整个“塔希提时期”,高更的艺术作品都具有非凡的意义,他把对土著人的观察和解读自然地融入了画中。高更一生中最多、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塔希提岛上完成的。塔希提岛为高更提供了十分广泛的素材。在最初的几年里,高更体现出了对当地女子的沉迷,他常凝视着坐在海边无所事事的塔希提女子,她们身体健壮又充满野性美,这和西方现代环境中的女性形象全然不同。高更用画笔将她们描绘下来,其中一部分是裸女,但她们既不拘谨也不做作,而是呈现出一个人最真实、原始的状态。中国台湾画家蒋勋在“破解高更之美”时评论道:“再一次凝视他画中的荒野、原始的丛林和海洋,果实累累的大树,树下赤裸的男子或女子,他们在文明出现之前,还没有历史,因此只有生活,没有论述??”高更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原始味道的艺术。在塔希提的高更博物馆内观赏高更画作
年上映的法国电影《高更:爱在他乡》,描写了向往原始、自然生活的高更来到塔希提后发生的故事。高更在绘画时也会引入《圣经》的内容,在《美妙的大地》(Terredélicieuse)中,他把夏娃的形象与塔希提岛的女性完美结合,因为宁静恬淡的塔希提就是她们的伊甸园。他从土著女友那里听过很多神话故事,常把塔希提人的形象融入到创作场景之中,《月亮和地球》(LaLuneetlaTerre)、《神秘之水》(EauMystérieuse)等画作中的人物似乎与这种浓郁的神秘气息有着天然的契合感。《亡灵的注视》(Lespritdesmortsveille)便是这样一幅极有意味的画作,高更曾在一封信中详细记录了创作它的过程。一天深夜,当他回到自己的小屋时,看到泰瑚拉非常害怕地躺在床上,可能是错把他当成了传说中的鬼怪或幽灵。为了表现这种恐惧,高更用了紫、深蓝和橙黄色,“渲染出在葬礼上丧钟敲响时和谐、黑暗、哀伤却使人警觉的氛围”;他在背景上添了几朵花,使它们看起来像四处迸溅的火花,因为在毛利人的思想中,夜晚的磷光就是死者的亡魂;最后,他画了一个鬼魂,就是一个普通年轻女子的形象。这些看似普通的意象叠加起来,恐怖之感顿显。《月亮和地球》描述的是波利尼西亚神话故事,月亮女神恳求地球神赐予人类永恒的生命,遭到拒绝。
《神秘之水》中高更将杂糅的色彩巧妙地和背景融为一体,增加了神秘感。
画作《亡灵的注视》的灵感源自高更真实的生活经历高更最震撼人心的画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是他在决定自杀前倾尽所有精力创作的。彼时的他,身染梅毒,爱女去世,排山倒海的痛苦将他推入了绝境。高更决定自杀,可是命运弄人,几次自杀全部失败。在最后一次自杀获救后,他看开了许多,画下了这幅他一生的巅峰之作。作品以塔希提的自然环境为背景,以长卷的形式从右到左依次讲述了人的新生、成长、死亡等阶段。右下方睡着的婴儿代表了新生,3位女性代表纯真善良;画面中间一个采果子的年轻人,象征着人类的中间发展阶段;左下方蹲坐的一个蜷缩着、抱头、满头银发的老人,则象征着生命的尽头。画面的背景是塔希提岛上的普通风景,场景也都是岛上原始部落生活中常见的情景,未加过多的修饰,却是一幅有关生命的哲学作品。到塔希提后,高更对色彩的运用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欧洲时,他总是对颜色把握不定,会“吹毛求疵”,但他在岛上速写时越来越意识到,其实在画布上“自然地涂上一种红色和一种蓝色”十分简单,纯色更接近土著人的纯真和质朴,也会使画面的冲击感更强。他开始大胆地采用装饰性图案和强烈的色彩效果,用简单而恣意的笔触和粗放的轮廓线去表达他对原始、粗犷古拙的美的追求。例如,在他年创作的《你何时嫁人》(Quandtemaries-tu?)中,他仅仅用蓝、橙和绿色在画面上互相衬托,从而使画面中的主角——两名塔希提当地女性更加显著,她们若有所思的眼神,不禁使观者对其心意有了猜测之兴趣。年,这幅油画以近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73亿元)成交,创下了艺术品成交价之最。高更代表作之一《你何时嫁人》曾创下艺术品最昂贵成交价格纪录。可以说,是塔希提造就了高更,他在这里确立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在世界绘画史上的艺术地位,并对现当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反过来看,高更也让塔希提更富色彩,他的画作和手记让塔希提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作家毛姆在年轻时就被高更和他在塔希提时期的画作吸引,后邀请秘书杰拉德一同来到岛上,通过各种各样的人了解高更过去的生活细节,回国后,他以高更的生平为素材创作了《月亮与六便士》。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思特里克兰德的灵魂一直都在他的身躯之外到处漂泊,四处寻找安身立命之所,最后,在这个遥远的国度里,终于进入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躯壳。用一句老话来说,他在这里可谓是‘得其所哉’。”是的,高更在塔希提也正是“得其所哉”。延伸阅读《月亮与六便士》背后的高更,疯狂而伟大
本文节选自年6月刊如果您错过了《世界知识画报》年征订期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即可订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