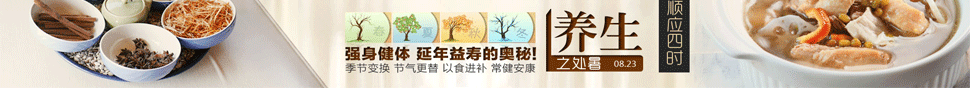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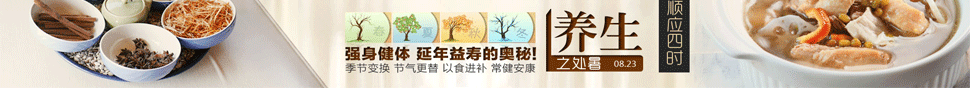
李金钟编辑
燕子图片
网络天还未明,村庄仍笼罩在蒙蒙的夜色中,街道还没显出轮廓,朱贵便从一处废弃的老房子里钻出来,骑上他那辆蓝色的破旧的脚蹬三轮车出发了。这两天天气比较好,寒气已经慢慢消退,天气慢慢转暖,不冷不热,没有蚊子,对朱贵来说,这是捡破烂的最好季节。朱贵的目标是附近的几个村庄。眼下农民的生活环境逐渐改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家中的废弃物越来越多。为了改善街道环境,村里绿化了街道,设置了很多垃圾桶,捡破烂也好捡了,当然也不排除村庄周围的坑塘、沟渠,被风刮着到处跑的塑料袋,被丢弃的废铜烂铁。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去城里了,天一热,地摊摆起来,被扔掉的啤酒瓶矿泉水瓶也多了起来,况且城里的生活条件好,各小区垃圾桶垃圾箱里宝物更多。但县城也不大,一天两天就能把城里转个遍,况且干这个基本不费本钱的营生的竞争对手也多了,要想拾个盆满钵满也是不可能的了。而现在不比当年,当年孩子娘还在的时候,他还有个伴,现在只能一个人起早贪黑云游四方。朱贵老家是河北云水县北河村,想当年老伴和他一起省吃俭用千辛万苦,农忙时种地,农忙过后就出来捡破烂。他们有两个孩子,朱贵两口子顾不着他们的时候,孩子就自己做饭吃作伴上下学,平时不用管,孩子很争气,考上大学后又分配了不错的工作,大儿子去了上海一家外企当白领,二儿子考上了公务员,在南京一个区里工作。朱贵觉得这样很好,虽然离家比较远,但两个儿子工作所在的城市离得比较近,生活上也好有个照应。终于把两个儿子供养成人,他们也比较争气,总算出人头地,还在当地娶了媳妇买了房,从谁心里来说都喜不自胜,值得骄傲,再苦再累,好日子指日可待。捡破烂累了歇息时,朱贵常常想到这些,想到令人骄傲的儿子,朱贵黢黑风裂的脸庞上总是洋溢着笑容,在笑容里慢慢入睡。可是好景不长,由于老伴积劳成疾,俩孩子成家后便撒手人寰,两个孩子回来自然哭得个死去活来天翻地覆。丧满之后,俩孩子便又各赴前程,回到了大城市。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希望朱贵能去大城市跟他们一起生活。但朱贵在农村劳动惯了,怕自己适应不了城市生活。后来两个儿子多次邀请朱贵前去南京上海小住几天,朱贵想想还是算了,老家离儿子工作的地方那么远,自己要是走了,那二亩薄田该怎么办呢?朱贵思想斗争了一番,还是决定留在家里,一是自己还能动,捡破烂还能锻炼身体,加上二亩薄田还能养活自己;二是,两个儿子都成家不久,需要工作又没时间陪自己,他们还没积攒多少家业,是否有地方住也是个事;另外自己除了种地什么也不会,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还可能是个累赘,净添麻烦,谁知道两个儿媳是否会喜欢自己,儿媳毕竟是外人;再说等自己年纪大了,再去熬煎他们也不晚,自己通过捡破烂攒点钱,到时候还能帮衬他们一下。朱贵向孩子们表达了这个意思,就继续留在农村老家,儿子们倒也没刻意挽留,孩子们会在过年过节回来看望他,但由于离家太远,他们平时根本没有时间回来。有时候孩子忙于工作抽空回来一趟,朱贵却走得远回不了家,慢慢地便都回家无定日,慢慢地孩子们两年三年也不回来一趟,但他们给朱贵留下了住址,好让朱贵在老家住烦的时候去找他们。虽然留在老家,不会给孩子添麻烦,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感觉自由一些,不过有时候,朱贵也感觉孤独了些。在家的时候,朱贵孤独了就去找老光棍李三叔去拉家常,歇两天然后又出发去捡破烂。朱贵又开始了以前的营生,重操旧业,他收拾好以前和妻子一起用的一直陪伴自己的那辆辆蓝色的破三轮车,又开始了走村窜巷的拾垃圾营生。村口一堵败墙前,李三叔在那里晒太阳,还有很多村民在那里拉家常,拉家长里短,都笑着说:“孩子也都出息了,你也该享享福了,还拾它干什么,那么辛苦!”朱贵只是憨厚地笑笑:“还能动,闲也闲不住。回来也好给李三叔买点好吃的。”然后就上路了。朱贵的战场主要是垃圾桶垃圾箱垃圾堆,他一不偷二不抢,别管饮料瓶塑料袋破纸箱烂鞋底还是废铜烂铁,凡是能换钱的东西都被他收入囊中,拾满了便就近找个废品收购点卖掉,好运气的时候能卖三十五十的,运气不好的时候也就几块钱十几块钱,他把钱都装在衣服内袋里。家始终是牵风筝的线,是人的牵挂,是人的魂,是梦,穷家难舍,朱贵有时候三天两天回家一趟,有时候一周两周回家一趟,慢慢地离家越来越远,回家的路也越来越漫长。但他每次回去的时候,都要给李三叔捎点好吃的,找李三叔拉拉呱。李三叔像是他唯一的亲人,他是李三叔唯一的陪伴。但朱贵自己是极简朴的。开始出去的时候,朱贵就捎两个馍带点自己腌的咸菜,吃完了就在附近馍店里买两个馍,后来卖了钱就买两个包子犒劳犒劳自己;捎个水壶,喝完了就给人家要点水喝。天黑了就去街上转,街上有路灯,天晚了,夏天就在公园啦桥下啦歇息,冬天就找个柴垛,下雨天就在人家的门楼下,或者找个无人的破房子避一避,挡风挡雨也挡寒。他不舍得吃也不舍得穿,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有时候拾破烂,看到人家扔掉的旧衣服回去洗洗就穿了。这样风里来雨里去,栉风沐雨,寒来暑往,风餐露宿,朱贵一干就是十几年。朱贵吃尽了苦,人也慢慢变老了,行动也不很方便了。但让朱贵感到欣慰的是,他每次回来后都会小心地在棉袄里子上缝个口袋,再把钱缝在口袋里,他棉袄的里子上口袋越来越多,棉袄越来越厚,也越来越重。破棉袄不引人注意,但他看到的时候很兴奋,心里也很清楚,这是个秘密,谁也不知道的秘密。终于在一场病后,朱贵感觉自己苍老了,夜里他把棉袄里的口袋拆开,数了数钱,足足有二十一万,这是他一二十年来的漂泊,用心酸和苦楚换来的,还有家里卖余粮后的积攒。灯下,朱贵数着钱,不禁感慨万千,但他有个决定,他要去熬煎他的儿子了,他需要他们的服侍,他需要过一段安安稳稳的日子了,他需要一个温暖的家来安度晚年。他要把自己辛辛苦苦攒的钱交给两个儿子,让他们补贴家用,他们在大城市里一定也不容易,大城市里消费高啥都贵,自己这点钱对孩子们来说虽然不多,但也许能救一时之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朱贵收拾好衣物,装在一个编织袋,然后用一个破褂子把钱裹住放在衣服中间,钱用布制品裹住不容易窜动,放在编织袋里也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朱贵对李三叔说:“我要去南方了。”李三叔先是高兴继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凉:“去吧,该去享享福了。”朱贵也有些无奈和犹豫,笑得皱巴巴的:“你要照顾好自己。我会回来看您的。”李三叔比以前更苍老了些,好像要生场大病的前奏。朱贵把家里安排给李三叔照顾,把二亩薄田也送给了他,收了庄稼还能换点钱,年过花甲孤苦无依的李三叔正用得着。朱贵跟李三叔告了别,在他那无神无助的视线里,扛起编织袋,带了被褥,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他事先没有通知两个儿子,他想给他们一个惊喜。这么多年,孩子们一定在心里牵挂着他,朱贵倚着火车车厢的过道想。他都没舍得买个卧铺,他只要个站票,他认为站票比坐票便宜。火车一路奔驰,朱贵望着火车的窗外,很多高楼大厦在火车两边一闪而过,这些都令他感到新奇,但他突然又感到心里很不安,到了南京怎么住,这些高楼大厦肯定不安全,万一趴窗户边一下掉下去,或者说站在那阳台上一下塌了怎么办。他又开始排斥城市了,他觉得城市和他是格格不入的。他风尘仆仆地到了南京,下了火车,便按照大儿子原先告诉他的地址找过去,一路打听,幸好住址未变,他来到了一个高档小区。小区里高楼林立,直耸云霄,绿树成荫,小桥流水,池塘亭榭,绿化得像公园一样。当他站在那巍峨的大楼下,便有一种压抑的窒息感袭来,大楼好像俯下身子打量着他这个陌生人,好像随时要向他扑过来,他非常感叹:“世道变化真快啊,环境不错,但这要是地震了,该往哪跑呢,住这么高?”这时他有点自卑,他觉得自己那土头土脑的形象土里土气的着装和那乡里乡气俗不可耐的行囊,与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和这个雍容华贵的小区有点格格不入,以至于坐电梯时都胆战心惊,害怕突然停下悬在半空或者一下子掉到底层去。到了十八楼,下了电梯,当朱贵敲开门,大儿子和大儿媳先是一阵惊喜,大儿子说:“爹,你终于肯来了!”大儿媳说:“爹,你咋来了?”然后就沉默了,也许十几年的分离让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许十几年的隔阂让他们不知道从何说起。大儿子把行李接过来放到沙发上,大儿媳倒上水,然后就去准备午饭。大儿子给二儿子打了个电话,二儿子说了客套话,但上海到南京尚有一段距离,二儿子说等工作不忙了就过来。大儿媳建议朱贵先在附近的宾馆里住一夜,洗洗澡理理发刮刮脸换换衣服,大儿子说:“这样也好,咱爷俩先拉拉呱,这么多年您也不来,我们都很想您的。”说着说着眼圈发红,几乎要掉下泪来。朱贵在大儿子家安顿下来后,总无所事事,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客厅里看看电视,要不就是在房间里干坐着,孩子们啥也不让干啥也不让摸,只有孙子回来还能喊个爷爷好,但说不几句就得去写作业,这一写就是半夜阑珊。住了几天,朱贵总感觉很拘束很压抑,甚至无聊。他总感觉大儿子家的气氛很沉闷,大儿子大儿媳并没有多少话,每天就是吃饭、送孩子上学、上班,家里总是剩下朱贵一个人,朱贵也不出门,外面的环境也不熟悉,邻里也都不认识。虽然行李放在储物间,但朱贵总爱枕着他的编织袋睡,虽然大儿子给他换了松软的绣花枕头,但他执意用他的编织袋换下来,他说他在老家枕着编织袋睡习惯了,这样他才有点安心,大儿子无可奈何,但大儿媳看编织袋的时候总鄙夷不屑,愤愤地,脸色很不好看。夜深人静,朱贵躺在床上总觉得哪里不对,他非常感叹,有时至于泪水沾湿了编织袋:“看样自己在这里并非长久之计,儿子一家对自己并没有多少感情,亲儿子也白搭,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还是扛着包袱回家养老吧,反正也饿不着,家里还有个邻居李三叔可以说说知心话。”想到邻居李三叔孤孤单单那凄凉的晚年,他又是一股老泪奔涌:“也许自己回去还能和他拉几年的呱,也许一个人也很好,无牵无挂的,啥也不用考虑。”他想到这里的时候,喉咙里有些哽咽。朱贵就这样想着,辗转反侧,许久才含泪而眠。第二天吃过早饭,朱贵便告诉大儿子大儿媳,他想到二儿子家去一趟,去住几天。大儿子听了很是感慨,百般挽留之间,大儿媳主动提议:“去住几天也好,提前去熟悉熟悉环境。您在我们两家轮流着住也行,再说他是老小,也该在他们家多住几天啊。”大儿子张了张嘴,不好再说什么,朱贵就去整理铺盖,把衣物按来的时候装好,然后大儿子开车把朱贵送到车站,买了车票,朱贵无言地去了上海。由于出发前大儿子提前给二儿子打了个电话,二儿子开车在火车站出口接了朱贵。父子见面,除了简单的寒暄,别无他话。二儿子家住的是单位的家属院,六层小洋楼的三楼,虽然没有电梯,没有大儿子家的高楼洋气,但家中也整洁大方干干净净,装修并不比大儿子家差。二儿子帮忙拎着行李,进了门,二儿媳喊了声“爹来了”,就把朱贵的行李搬进了杂物间,把朱贵安排在了北面的小书房。小书房里的单人床上早已铺好新铺盖,靠东墙一溜书橱,还有一个写字台,写字台上堆了很多文件和资料,看样有时候二儿子得在书房里加班写材料。书房很小,但一张床还能容纳下朱贵,睡觉也就是占一席之地,其实人就是死了也不过就占一席之地,并不用多大的地方。朱贵几次要求把自己的行李搬过来,都被二儿子二儿媳拒绝了,朱贵几次偷偷地搬过来,又被搬了回去,二儿媳有点生气地说:“你那些破衣服破铺盖就别要了,回头都给你买新的。你这破玩意儿在书房,家里来了人有伤体面。”朱贵也不好说什么,最终还是要求把编织袋枕在头下,他说他在老家枕着编织袋睡习惯了,不枕不舒服,怕会得病。夜里,朱贵自然难以入眠,朦胧间,他隐隐约约好像听到二儿子二儿媳房间传来嘟囔声,朱贵侧耳,但具体的话却听不很清,大体是说脚臭味,至于说的谁也不清楚。不过在朱贵看来,大儿子家二儿子家条件自然好,但和自己家的味道也差不哪去,走到哪里都有股脚臭味,还嫌人家脚臭!第二天饭后,朱贵看到客厅的阳台空间大,还有花盆,终于找了个吸烟的地方,二儿媳便皱着眉头说:“爹,别吸了,家里有烟味,不光污染了空气,对大人小孩的健康也不好。”朱贵“嗯”了一下:“没事没事,我就抽一颗。”二儿媳白了他一眼,气鼓鼓地走开了,收拾东西送孩子,然后上班去了。由于朱贵占用了书房,有时候二儿子只得在卧室里写材料,有时候一写就到十二点下一点,自然影响了二儿媳休息,她又在那里小声都都囔囔地吵:“孩子第二天还得上学呢,你在这里写材料,影响了孩子休息,就影响了她学习啊。都怪你爹占用了书房!”只听见二儿媳压低声音说:“你看看跟你爹商量商量,他要是在这里常住,咱出去给他租个房子好不好?”二儿子也压低声音,好像很为难地说:“这样不好吧?”二儿媳有点要急的意思:“啥不好的?这样啥事都解决了,你想想。”然后就是一片寂静。朱贵心里一凉,非常的难过,又是半夜无眠:“这不是嫌弃我吗?这不是要赶我走吗?我老家有房子,我何必在你们这里租房子啊!”第二天吃饭的时候,二儿媳不停地给二儿子使眼色,二儿子吭哧了半天才说:“跟您老商量个事,如果您要打算在这里长期住,您看在这附近给您租个房子行不行,租近点,也好照顾您,您只在那里睡可以来这里吃饭。”二儿媳忙补充说:“这样都方便,租房费您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和大哥家均摊。”朱贵脸色很沉郁,但装作无事的样子,他把碗筷放下,抹了抹嘴:“不用了吧,我准备在这里住两天就回去,家里的庄稼也快收割了,在这里我也住不习惯,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有时候闷得慌。咱那个邻居,你孤身一人的李三爷年岁大了,正好需要个人陪陪他了,我回家他还有个照应。”朱贵拿眼看了看窗外,似乎就不准备把视线抽回来了:“我在农村摸滚打爬生活了大半辈子,天天和庄稼打交道,我离不开庄稼离不开农村,人家都说叶落归根,反正我死了早晚得回到农村。”二儿子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语音哽咽地说:“您说什么呢。”朱贵似乎很想得开,不以为然地苦笑了一下:“你们有工作都很忙,你们忙吧,我在这里只能耽误你们的事。只要你们都能照顾好自己,能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也就放心了。”晚上,朱贵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仰天长叹,老泪纵横:“养儿来防老,没想到养了两个儿子,到头来一个一个嫌弃。一辈子啥事都靠自己,到老了也得靠自己,亲儿子也靠不住啊!”第二天起来,朱贵就把行李收拾好,但笨手笨脚的明显感觉苍老了些。吃过早饭,二儿子给大儿子打了电话,大儿子在电话中极力挽留,但由于工作没法赶过来,就由二儿子把他送到车站买了车票。城市对朱贵来说本来就是陌生的,此时依然十分陌生,所以朱贵一点也不留恋。走的时候,二儿子二儿媳也没刻意挽留,只是说有空再过来。朱贵心想:“再过来,还要把自己的心再伤一会?哼,算了,不知道自己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城市不属于朱贵,他扛起行李,带上思念,挽回希望,踏上了回家的路。火车上,朱贵一度陷入沉思,火车两旁的高楼大厦不停地扑向他又远离他,窗外的世界不停地变幻,他还是那个他,不过年纪越来越大,家还是那个家,他只有一个!极度失意中,疲惫不堪的朱贵回到家,看着自己那破旧而熟悉的小院,他倍感亲切,比看到儿子还亲切,以至于激动地嚎啕大哭,那小院就是生他养他的母亲,孩子见到母亲总是止不住流泪,好像有天大的委屈。哭声惊动了邻居李三叔,李三叔拄个拐棍弓着腰颤巍巍地来到朱贵家里,用苍老沙哑的嗓音关心地问:“怎么了朱贵,是丢了钱还是丢了什么,一把年纪了还哭啥?”朱贵用长了层老茧的手抹了抹那浑浊昏花的眼,嗫嚅着:“没有没有,我这是看见你亲切啊。三叔啊,我也差不多和你样孤身一人了,我们相依为伴,慢慢熬吧!”李三叔叹息了一声:“哎哎哎,我这无儿无女的。孩子都不认你了啊?”“也不是,认是认,只不过这年月,时光确实容易把人抛,你看门口路边那芭蕉绿了红,城乡还是隔离了亲情。这还都是亲生的,就嫌弃爹了……哎,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以后咱俩相依为命吧。”李三叔一边感叹,也一边感动得热泪盈眶,禁不住掏出手绢擦了擦眼。以后,朱贵有空都帮助李三叔刷锅做饭,做家务,找他拉家常。过了两年,在一个庄稼正疯长的季节,李三叔病重过世,朱贵为他简单办了后事,谁叫他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呢!之后,大儿子也打过电话,还是希望朱贵能去大城市跟他们一起生活,他们也能尽一份孝道,让朱贵过个幸福的晚年。“幸福的晚年?不忧郁心烦死就不错了。”朱贵还是觉得不妥,“还是等等再说吧,我能把自己照顾好,你们好好生活。”又过了两年,朱贵也感觉自己精力不济,他又有了一个决定,在一天夜里,他偷偷地把钱从编织袋的破褂子里取出来一部分,剩下的还缝在破棉袄里子的一个个口袋里,然后带了行李去了乡镇敬老院。敬老院有一二十个老人,老人们吃完饭就在院子里晒晒太阳,谈谈天说说地,下下象棋听听戏,连衣服都不用自己洗。但朱贵总是觉得不如意,看人家下象棋也心不在焉,因为他和很多孤寡老人不一样,他是有儿子的人。朱贵心神不定地在敬老院过了一天又一天,除了按月向敬老院交钱,他也花不着啥钱,他根本不需要儿子们的钱,他也不向他们张口要钱。又过了两年,风烛残年的朱贵得了一场重病,他脸色蜡黄,身体也越来越瘦,非常虚弱,他叫服务人员把院长叫来:“院长,在我死之前,我有一个重托,我还有一部分钱,我把剩下的全部捐给敬老院,希望让更多的孤寡老人生活得更好一些。”他费力地把棉袄从编织袋里拿出来,又费力地把棉袄里子上的口袋一个个拆开,一堆钱就摊在众人面前,院长派人整理点数,足足还有十五六万块,院长、服务人员以及院里的老人们都有点呆了,不知道如何是好。院长关心地问:“朱大爷,您没有孩子?”朱贵有气无力擦了擦泪,倚在床头:“我虽然有两个儿子,但我就像个孤寡老人。他们也都用不着我的钱,我也就捐了吧。”在场的人也都不再出声,默默含泪,瞬间起敬。在院长的再三劝说和请求下,通知了朱贵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及儿媳妇接到消息后大惊失色,请了假,火速赶来,看到一如死灰般的父亲,望着摆在床边的钱,羞愧难当,懊悔不已,他们泣不成声:“我们没有照顾好您,让您受苦了……”朱贵已气息奄奄,紧闭着眼一句话不说,眼角两行老泪溢出。良久,朱贵伸出骨瘦如柴的手,颤抖着摆了摆:“不说了不说了,路是向前走的,无法回头,我已经走到尽头了,你们还要好好的生活。”朱贵有气无力地顿了顿,“不过,这是我一生捡破烂攒的钱,我还是打算把它们捐出去,我想让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们过得舒坦些。”儿子们已哭得失了声,不停地擦着泪,遵照朱贵的口头遗言,当着众人的面在捐赠协议书上签了字。弥留之际,朱贵把孩子们叫到床头,嘴里念叨着:“人死归土,死后也就无所谓城市乡村了,也就融入到世界中了。俗话说得好,啥事都得靠自己,你们以后得靠自己努力了。”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说:“虽然我死了,但我还是牵挂着你们的。”朱贵死后,由于他的捐赠,在敬老院院长的主持下为他开了追悼会,儿子儿媳们哭得死去活来。这时候距离邻居李三叔去世正好六年,又是庄稼在地里疯长的季节。作者简介:李金钟,山东省菏泽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菏泽市作家协会会员,牡丹区作家协会会员,青年作家网、《作家前线》签约作家。94年就开始写现代诗,然后开始写散文,由于工作和生活,其间荒废了二十多年的时光,但愿天荒地老有人识。下定决心,不为媚俗,只写纯文学。喜欢旅游,有生之年,无忧无虑游天下。壹点号心梦文学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limaalm.com/lmfz/1230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