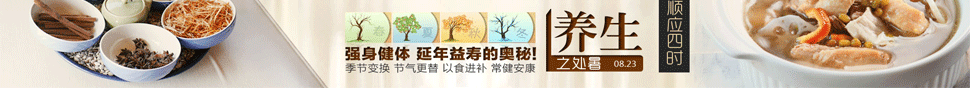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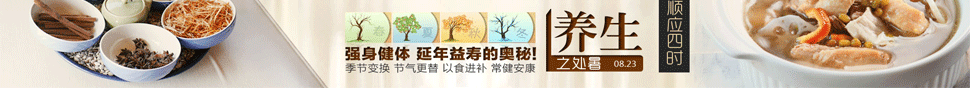
运动暴力之观众暴力:微观社会学理论
摘要:可将观众暴力分为有赖于比赛的观众暴力和发生于场外的观众暴力。有赖于比赛的观众暴力有观众闯入球场,观众向场内掷物,观众和选手对打,观众和观众互殴等形式。选手在打斗时,双方地位基本平等,大致属于公平竞赛;而当选手打观众及观众打观众时,双方势力严重不对等,只能说是恃强凌弱。可将发生于场外的观众暴力分为庆祝之骚乱和失败之骚乱,这两种骚乱也都有可能是政治骚乱。足球流氓是作为精巧技术的场外暴力:大家精心设计运动项目,以让球迷产生情绪上的共鸣以及群体性的团结;流氓精心设计流氓暴力,以让打斗帮助他们产生共鸣并加强团结。对足球流氓而言,情境化的技巧既是他们行为的关键,也是流氓行为魅力的来源。足球暴力最早在20世纪早期出现在英格兰。现在,足球暴力遍布世界了;但那些最暴力的骚乱,反倒远离英国足球流氓的行为轨道。足球暴力还与看台的形式、交通方式有关。大众商业娱乐时代同时也是表演者统治的时代;无论是朋克的社会技术,还是足球流氓的社会技术,都是观众反抗演员/选手以进入行动中心的方式。
关键词:微观社会学理论;运动暴力;观众暴力;足球流氓;
作者简介:兰德尔·柯林斯李睿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丽水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1有赖于比赛的观众暴力
观众暴力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粉丝闯入球场,粉丝从远处掷物击中选手,选手和观众对打(尽管很少见),还有粉丝在比赛进行时互殴。
最后的那种暴力形式,即粉丝打粉丝,在之前的研究中尚不多见1。有些球场之所以著名,就因为其某些看台区域打斗事件频发。例如,费城老兵球场(已于年拆除)中那些比较靠上的便宜座位,就是那些小流氓既丢东西乱砸、又甩膀子互殴的地点;他们还强烈反对客队球迷到那个区域看球。我们尚不清楚这些打斗到底会如何影响场上比赛的节奏。有些球场以盛产粗暴球迷而著称于世,主要位于东北部的几个大城市(特别是波士顿、纽约和费城,集中于职业橄榄球和职业棒球比赛),同样是观看这些运动项目,但西海岸的球迷就没那么暴力:他们在喝彩时,没那么疯狂;他们在喝倒彩时,也没那么尖刻。通过观察,我发现了如下的规律:那些暴力频出的球场,主队的球迷多数是年轻男性;而西海岸及中西部地区的人口中,女性或有家庭的人士占了更大的比例。北美冰球观众和橄榄球观众(主要由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人士组成,其中将近一半是女性)和欧洲足球比赛的球迷(其中很多是17—20岁的工人阶级男性)相比,两者在暴力方面的差异,也能用同样的道理来解释(RobrtsandBnjamin)。观众间有时会爆发小规模的打斗,参与这些打斗的人有时支持的还是同一支球队,我们尚不清楚这些打斗会在何时发生,也不知道发生的频率如何———可能频率很低,因为球场之所以充满暴力的气息,正是因为球迷支持的是不同的球队。
大家一听到观众暴力这个词,首先想到的就是大规模的群体性骚乱。有位研究者收集了多伦多报纸全年报道的所有群体性暴力事件(统计范围囊括所有项目),发现其中有27次(占74%)源于选手的暴力行为(Smith)。例如,在一场冰球初级联盟比赛中,发生了一起双人交叉撞人事件,这最终引发了一场大混战。参战人员包括:差不多两队所有的球员,几百名观众以及二十名市警。在布法罗与克里夫兰的职业冰球比赛中,观众看着球员打架,突然就乱掷起椅子来了,椅子就在球员头上飞来飞去,球员操起球杆,跑上看台与球迷交战。在多伦多曾有场足球赛,比赛双方是南斯拉夫萨格勒布队和希腊全明星队,到了下半场第18分钟,有多名观众闯入球场。当时比分是1比1平。之前希腊球员带球奔向球门,被南斯拉夫队的门将踢倒在地。裁判判罚点球,门将上前抗议。这时两队球员互相推搡,然后球迷跑入球场。这些观众猛踢球员(注意:球迷重现了球员的动作),球员则以老拳回敬对方。双方球员及双方球迷的群体文化对抗,构成了这场打斗的结构。不过在这场打斗爆发的时候,比赛也正处于转折点,因为点球可能会决定比赛胜负:比赛过半,比分相同,这正是最紧张的时刻。此时球员和裁判争执,打破了比赛的结构,球迷冲入球场。直到大批警察前来干预,这场战斗方告结束。
和球员一样,球迷也是比赛戏剧节奏的俘虏:虽说球迷主要是为了经历这些紧张刺激的场面;同时聚在一起,也便于表达他们共同的情感———这样他们就会共同欢呼,上下团结,比赛才会与每个球迷息息相关。因此,这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当球员彼此大打出手,球迷此时也在贴身肉搏2。不同的运动项目全都适用这个规律:心理测试显示,当球迷看完橄榄球或冰球比赛,他们会变得更加好斗———我推断当他们在看比赛时,他们的心理反应也是如此;不过,如果是刚看完体操比赛或游泳比赛,他们并没有以上的反应(GoldstinandArms,;Arms,RussllandSandilands)。粉丝的情绪流,是随着不同游戏的不同特点而不断变动的。如果某些暴力行为看起来戏剧感十足,又被用得恰到好处,这些暴力行为正是比赛行为的合理延伸:仅当球迷认为对手是在故意施暴的时候,他们才会变得不依不饶(Zillman,Bryant,andSapolsky);而当球迷认为球员的受伤纯属意外,那他们不仅不会无事生非,可能其行为还会有结构性的变化———球迷反而会向敌队那位受伤的球员鼓掌致敬。
当球员和球迷直接对打的时候,那个球员或球迷必须跳到对方的地界上去。有时候大批球迷攻占了球场,这时他们往往希望扰乱比赛,好让比赛早点结束(或者因为比分领先,或者因为球迷对比赛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不过他们有时也想借机攻击裁判。不过,如果只有个别球迷闯入了球场,球员也很可能对他们拳脚相向:因为正是凭着暴力,球员才获得了广大球迷的支持。
与球迷相比,球员才是暴力精英:多数严重的球员球迷对打事件,常由球员率先攻击球迷而开场,往往是因为球迷喝倒彩,球员就跑到看台上用拳脚回应。不过,喝倒彩在比赛中也算稀松平常,而且无论是谁,只要身为球迷,就算自己的举止充满敌意,他也会希望逃脱处罚,他甚至还会因此而得到大家的支持;所以,如果球员毅然以暴力应对挑衅,那么在球员那里,一定还有某些特殊的压力。在第3章,我们看到TyCobb是在他要打破击球和偷垒纪录的时候,他是在这些压力下,冲占看台的。我还有些别的例子,在那些例子中,压力来自球队竞争时独特的戏剧结构3。
如果说两支球队“有过历史恩怨”,那就是说两队间有过戏剧化的冲突。那些历史故事每个球迷都耳熟能详,他们憧憬着将要到来的比赛,并把这些历史恩怨当成比赛看点。球迷都是寻梦者;戏剧中的暴力事件,到底是爆发还是不爆发,其实谁都说不准。之前,我们略微谈到印第安纳步行者队和底特律活塞队的关键历史:正是那次把人击倒在地的暴力事件,成了活塞队赢得东部冠军的转折点。两队在随后的赛季再次相遇,步行者队火力全开,想借此弥补因之前失败而造成的遗憾。步行者队球员RonArtst,在之前的东部决赛,他曾击倒对方球员,那一击确实让比赛进入了高潮,但却只是帮了对手的忙;这回,他又在比赛就要结束时,对活塞队最高大的那名球员严重犯规,并引发了接下来的打斗。这时比赛还有45秒就结束了,而他们又领先对手15分,所以这次犯规很有些不着调,除非我们说他就是要故意报复对手。那位步行者队球员显然视之为侮辱,他就使劲推了Artst的脑袋,这样两队球员就又在地板上小过了几招。Artst好像就是想让对方出丑,他就躺在边线旁的技术台上———既占了官员的地盘,又向世人炫耀了他的安全港;他的对手此时怒火冲天,但被人拉住了,没办法为自己伸张正义。随后,当两队在底特律的主场比赛时,底特律的球迷也学会了这招,当然更免不了一场由球员打架引发的球迷打架———这是标准模式。在震耳欲聋的嘘声中,有位球迷模仿Artst躺在技术台上的样子,用这个看似毫无防备的姿态引诱他靠近,随即拿起一杯冷饮向他砸去。Artst立马跳上看台,和他一起上去的还有一个队友,他们和两个球迷对打了一番;战火燃烧到了地板上,只见Artst出拳猛击一球迷,这个球迷穿着活塞队运动衫(好借此展现其幻想中的身份),之前是来和他搭话的;Artst又被另一个球迷扭住,不过这个球迷还要面对Artst的队友,只能轮番作战。混战以步行者队球员退场告终,这些球员被球迷弄得勃然大怒,但他们只能看球迷安然无恙地待在看台上。比赛剩下的时间就被取消了(《费城问讯报》,-11-21)。
这场打斗经媒体曝光,引发了轩然大波,大家倍感震惊,纷纷谴责此事;还有几位步行者队的球员被联盟长期禁赛。但在事实上,这场打斗的每个元素都符合运动暴力的一般规律:那些最喧闹的球迷要竭力挑起戏剧冲突,这也引来对方球员以暴力相报复———据我所知,这个案例和其他球员球迷间的暴力事件没什么区别。尽管如此,比赛官员和评论员的反应却都差不多,这说明了运动戏剧的基本结构:运动戏剧是为了观众的需要而上演的,而观众大都希望在受保护的情况下,积极介入这些他们幻想中的冲突。观众的地盘和选手的地盘必须泾渭分明,这是整个演出的结构性要求:选手间的暴力行为,无论这些行为是合乎规则的还是违反规则的,都被限定在选手之间;而观众反对选手,他们的暴力大多带有相当的幻想意味,行为也多停留在嘴上———要真打起来,选手施暴的水平可要比对方强得多。因此,选手必须将暴力限制在赛场内,而不能直接针对观众。
选手介入冲突的结构,和观众相比,是不一样的。因此,看到他们打斗的方式也不一样,那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选手在打斗时,双方地位基本平等,大致属于公平竞赛:无论是两名选手扭在一起,你一拳我一拳地互殴;还是两队人马在场内上演全武行。不过,当观众暴力爆发时,双方势力严重不对等,只能说是恃强凌弱:主队球迷会丢东西砸客队球迷,追打客队球迷;他们还会追打客队球员;在球场安保人员人数不足时,球迷有时还会攻击这些安保人员。
选手间的打斗和擂台上的公平打斗类似,参加打斗的选手也和那些决斗者类似。保证参加打斗的双方公平地竞赛,这本来就是精英所要具备的精神风貌。不过,观众可不是精英,他们会像骚乱中的暴民一样攻击弱者。当他们向敌队喝倒彩或掷物攻击时,对方就更显得势单力薄。在同一场冲突中,球迷和球员一样,既有情绪上的投入,又有象征上的投入。不过,两者的行为机制可不太一样:球迷用无耻下流的方式支持他们的部落战争1;选手则有如英雄,他们会按照光荣的传统,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对手搏杀。粉丝在狂热的时刻,宁愿在选手面前自贬身价,就像原始宗教信徒在参拜圣物;粉丝就像那些在公共派对的边缘地带饮酒狂欢的人。假如粉丝闯入选手的地盘,那选手的表现就会像精英驱赶来犯的庶民一般。选手就像贵族阶层,他们对内按照荣誉的法则解决争议,但如果是那些下人跑来惹是生非,他们就会抽出棍子,不由分说地将之暴打一顿:运动员会严惩那些入侵他们领地的人,会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我们会发现,正是因为选手和粉丝处于不同的地位,才让粉丝的暴力有了更加精巧的形式。
2场外粉丝暴力:庆祝之骚乱与失败之骚乱
运动场上的暴力事件,大多和赛场上对决的节奏有关。不过,也还有独立于赛场剧情的粉丝暴力,主要有三种,其中最极端的就是足球流氓的暴力———这种情况我到后面再谈。有几种观众暴力,或者始于运动场,或者刚开始时与比赛有关联,但随后暴力就溢到了场外,并发展为独立的暴力形式。这三种独立于比赛剧情的粉丝暴力是:政治暴力,庆祝之骚乱,失败之骚乱。
比赛中的政治暴力源于比赛以外的冲突,陷入国家(民族)冲突的双方本来相距遥远,但比赛为他们提供了近距离对抗的机会。那些围绕比赛的对抗也会加深政治上的仇恨,更凸显出双方的敌对状态。
例如,年在萨拉热窝举行了一场足球赛,波黑对阵南斯拉夫。自从年双方开战(这场战争因惨绝人寰的种族清洗而臭名昭著),这还是两队第一次交手。举办地萨拉热窝是波黑的首都,现场有一万左右的波黑球迷支持主队,还有三百来人支持南斯拉夫队,这三百人基本来自当地的波黑塞族。在播放南斯拉夫国歌时,波黑球迷跺脚示威;而在播放波黑国歌时,南斯拉夫支持者的回应就是朝对方露光腚。几百名警察上去把双方球迷分开。之后双方球迷就开始了朗诵比赛,南斯拉夫的支持者在不停地高喊“这是塞尔维亚”,“卡拉季奇,卡拉季奇”———卡拉季奇是被通缉的重要战争犯罪嫌疑人;波黑球迷则高喊“安拉胡阿克巴”,这是伊斯兰教传统的作战口号,意为“真主至大”。南斯拉夫队最终以2比0取胜。警方保护南斯拉夫球迷离开球场;此时有差不多两百名波黑球迷在场外袭击警察;有六名球迷及十九名警官因此受伤,另有八名球迷被捕(《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8-23)。
比赛,作为假想性的搏斗,会让人重温往日的政治暴力事件。赛事也会引发带有政治主题或民族主义的骚乱。年世界杯期间,俄罗斯足球迷聚集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广场上,通过大屏幕观看俄罗斯对日本的比赛,当日本打入了全场比赛唯一一球后,球迷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俄罗斯队赢下了上一场比赛,赛前各界也都更看好俄罗斯队,但球迷的希望却破灭了。大概有八千球迷,多数是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满大街地高喊:“前进,俄罗斯!”其中有些人,身上还裹着俄罗斯的三色旗。在一英里外的地方,他们打破了商店的玻璃,在车顶上蹦来蹦去,砸碎了车窗玻璃,还掀翻了十几辆车,他们还点火烧了7辆车。球迷攻击了五个日本学生,这几个学生是学古典音乐的,正要去附近参加音乐比赛。骚乱中球迷还丢掷酒瓶,互相厮打,另外还攻击警察。有一人死亡,大约五十人受伤住院,其中有二十名警察(《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6-10)。此案例中,对手入球的时机引发了大规模的暴力事件:球迷既袭击了日本人,也袭击了其他的目标。
这场发生在年莫斯科的骚乱,既是场政治骚乱,又是场失败之骚乱;与之对应的,就是因庆祝胜利而引发的骚乱。我们会发现:庆祝之骚乱,和失败之骚乱一样,破坏力都很强;而庆祝之骚乱的破坏力,比失败之骚乱还要强。因为如果比赛输了,总会让人泄气,球迷大多会情绪不振。这样,广大球迷就没心情(情绪)去搞那些传统的仪式(比如去扯掉球门柱)———正是这些仪式让欢庆胜利变成了破坏性的骚乱。失败之骚乱还需要额外的运行机制。这儿有条线索:与国内比赛相比,失败之骚乱似乎在国际比赛中更多———在国际比赛中,比赛对手被高度地政治化了。要发生失败之骚乱,总需要一些额外的因素———因为就比赛的情绪而言,其能量流动一般是从失败的一方流出,而流入胜利的一方。
胜利后的庆祝就是某种形式的饮酒狂欢1。球迷的胜利是情绪上的胜利,球迷的庆祝是球员庆祝的扩展形式。球员和球迷都有一些共同的团结行为:他们一起欢呼,互相拥抱,四处跳跃,以此释放肾上腺素———他们多少有些肆无忌惮,以便记录这特殊的时刻:获胜的足球队员把大杯的啤酒倒在教练身上,这种娱乐性的暴力行为转换了权威的角色,就算被球员作弄,教练一般也不会发火;美国职业球队如果得了冠军,队员会打开柜子里的香槟,但不是拿来喝的,而是倒在彼此的身上———这些行为类似狂野的派对,但造成的破坏却微乎其微。
球迷庆祝时的选择和球员不同,因为他们没什么接近球员的机会,没法和球员一起用肢体动作来展示团结。不过,球迷也有替代的办法,即去冲占篮球场或足球场。事实上,足球比赛胜利的传统仪式,就是在比赛结束时把球门柱扯掉(这源于20世纪初期的大学比赛,当时球门柱是木制的,近几十年的金属门柱就不太好扯断,但有人有时还是会试试)。球迷被吸纳到互动仪式的中心地带,在那儿他们接触到充满神奇意义的物质对象:掀起一块草皮(或一小块篮球场木地板,或座椅)作为纪念品带回家———这样,球迷就能获取神圣的对象并从中汲取魔力。庆祝胜利的暴力结合了两部分内容:夸富宴(值得铭记的狂野派对),以及进入行动中心的愿望。
不过,球迷并不是身处中心的精英;他们想得到信物好进行象征互动,但管事的一般还不让他们这么做:近些年来,运动场的负责人雇佣了大量的安保人员,好让球迷无论何时都进入不了场地。球迷庆祝胜利的方式就因此而改变了:从传统的、发生在运动场地上的夸富宴般的破坏,到发生在场外的大规模骚乱。随着场内安保不断加强,场外骚乱也在持续增加———该假设是能经得起检验的,无论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检验,还是拿不同安保水平的赛事来对比检验。
在下面的例子中,获胜的球队当时不在主场,但在主场的校园却发生了庆祝之骚乱。注意以下两点:这场暴力事件各阶段具体的时间,以及当时社会控制的举措。这两方面的信息都是很有用的:
年4月,明尼苏达大学冰球队在纽约州水牛城比赛,争取二连冠。在明尼阿波利斯,为了在公共空间庆祝胜利,兄弟会在草坪上放上了啤酒桶。晚上8点半,传来了胜利的消息,大家从兄弟会、女生联谊会、宿舍中涌出来,组成了一支上千人的队伍。不到二十分钟,他们就在十字路口燃起了篝火(在远离建筑的安全地点)———被烧的是一个床垫、一张公园的长椅。学生把这些东西一起放在一个大垃圾箱里烧。消防员迅速赶到,扑灭了火焰。当然,也中止了庆祝的活动。球迷随后又在四周的垃圾箱里生火———继续烧垃圾。在最初生火的街角,红绿灯掉了下来,有人悬在街道的大梁上,他还想用力把那个大梁扯下来。有位警察说这帮人“快活得好像是在参加运动会”———此话不假,因为他们就是要让观看比赛的体验延续下去。
此时两个警察面对一千个学生,人手不够。学生又向警察扔酒瓶子,警察只能撤退,回到巡逻车里。最后这些学生召来了两百名警察,双方都难以自控,局面升级:警察开车过来,但陷在人堆里面,反而被学生砸了车;消防车也不够用了,因为几乎每个路口都着火了。
警察每15人列成一队,站在两边人行道上。他们肩并着肩,走到路中央和这帮人对峙。有个警察拿着扩音器命令这帮人赶快散开,但这些学生的反应却不太快。“从路中央退场可没那么快”,有个大二学生对记者说,“那又怎么了?”
这么一大群人还是像之前那样没规矩,他们向警察扔酒瓶,还扔别的什么烧着的东西。警察现在要拿警棍赶人了,他们先后退,再分成三队,然后分别从三个方向进攻。警察花了十五分钟才扫清这个十字路口,然后消防车开来把火扑灭。之后,警察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继续镇守着这个路口。
与此同时,有人又在别的十字路口生了几堆火。更多的警察随后赶到,然后一一清场。这时是晚上10点半,警察还在面对三四百个学生。人群的规模是越来越小了,但这些人还是热情不减。有位目击者称:“这些人当时在高呼‘U-S-A!U-S-A!’”还有人在喊:“这就是巴格达!”这些学生借用了国际运动会的口号,当时是为了纪念美国冰球队在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中以弱胜强,击败了苏联队———现在则是为了庆祝美国军队年3月在伊拉克的胜利。
所有具有情感(情绪)纪念意义的象征,当时都会被立刻拿来运用———我到后面还会论证这个观点。当这些年轻人掀翻汽车时,他们欢呼雀跃。那些人先把报纸点着火,再把垃圾箱点着,再点着那辆被掀翻的汽车。许多人在用手机打电话,告诉对方自己的所见所闻。有位目击者听到这句:“老兄,你真该来看看这个,这真让我开眼了!”———喜悦的叙事和喜悦的行动混在了一起。
还有个地方,因为停车场里的岗亭着了火,有人打开了消防栓,街上到处都是水。警方把化学喷雾射到人群里,把不少人赶了出来。
到了夜里11点左右,有些球迷在踢大学运动馆的门,他们想破门而入。垃圾回收箱里又燃起了火焰。有些球迷甚至想点燃灌木丛。警察又拿警棍驱赶他们,他们便跑开了。
将近午夜时分,球迷向救火车扔酒瓶,救火车的挡风玻璃都被砸碎了。到了凌晨1点,最后一堆火才被扑灭。整场骚乱持续了五个小时。大学周边总共生起了六十五堆火,汽车被掀翻点着,有家店铺被抢了,玻璃被砸碎,道路上标志被扯下来了。为了保证庆祝的气氛,那些游行的去抢了家酒水店。警察赶到时,那家店的玻璃被一辆自行车砸开,抢店的早已逃之夭夭。目击者说那些抢店的扛着一箱箱的啤酒从店里出来。店主说:“他们差不多把所有的伏特加都抢走了。无论是便宜货还是值钱货,他们照单全收。”(《明尼阿波利斯星论坛报》,-4-20)
当火熄灭时,骚乱也就停止了;最开始只有一两处火点,最后发展到几十处火点———随着警察的态度越来越强硬,火点在不断地扩展。骚乱的行为,还有热烈的叫喊(看来就在头一两个小时达到了顶点),主要发生于他们寻找新地方生火的过程中。这些人生火烧东西的形式也都一样:烧烧垃圾或建筑废物。球迷没有点燃建筑物的打算(尽管在夜里,在被警察驱离十字路口中心的开阔地带时,他们也曾以此相威胁)。火,就是让道德节日(译注:关于“道德节日”,见该书第7章第1节)事态持续发展的主要工具。这些积极分子行为的一般规律是:人数最多时大约有一千人,这一千人出自大学城里约三万九千名学生,而且这一千人中还有一部分只是在那儿看热闹,而没有去制造骚乱。
庆祝时发生了骚乱,发生了袭警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球迷缺少类似夸富宴的传统节日:他们没办法在有限的范围内搞搞破坏———比如老传统中的扯球门柱,或点上篝火———好庆祝节日。现代社会缺乏在道德节日搞轻微破坏的制度化场所,这正是发生骚乱的原因之一。还有个原因,就是大众传媒让球队自己的庆祝得到了更多的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limaalm.com/lmjj/9228.html


